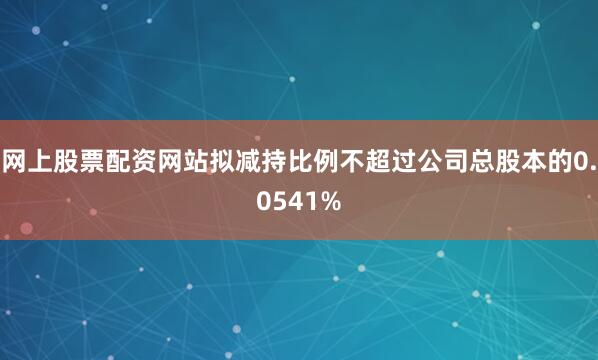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打破了1981年10月12日上午的宁静。警卫员拿着话筒压低声音汇报:“首长,中央又催您参加中顾委会议了。”房间里传出粗犷的声音:“告诉他们,我老许这身子骨不中用了,就爱守着这几分菜地过日子。”
这话听起来像是推脱,实际上却是许世友内心最真实的写照。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将军,竟然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迷上了种菜养猪的农家生活,连中央的会议都不愿意参加。
说起许世友这辈子,跟“安逸”两个字八竿子打不着边。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,从朝鲜战场到对越自卫反击战,他把大半辈子的精力都消耗在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。龟龟,越是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,他越是想念童年时代闻到的那股田野泥土香味。
1980年春天,上级决定让他离开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岗位,调到军委担任常委。按理说这是高升,可许世友心里却有另外的盘算。刚到任几个月,他就主动递交了退休申请书,给出的理由简单粗暴:“年纪大了,得给年轻人让路。”这种做法跟他当年指挥打仗一样,说干就干,毫不拖泥带水。
老爷子一旦拿定主意,八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妻子田普和几个子女轮番上阵做思想工作,摆出一大堆理由:北京医疗条件好、交通便利、一家人能团聚什么的。可许世友一句“南京那地方气候暖和,我想种点菜”就把所有劝说都堵了回去。
为这事,老两口还闹了三个月的“冷战”,甚至分床睡觉。田普后来无奈地摇头:“拗不过他,谁让这人是许世友呢。”

九月初的一天,南京中山陵8号的钥匙正式交到了许世友手上。这栋欧式小洋房原来属于孙科,四周爬满了绿藤蔓,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,怎么看都像西方贵族的庄园。
可许世友一踏进院子,第一件事就是指着那些娇贵的玫瑰花说:“全给我刨了。”然后招呼警卫员抬来锄头镰刀,开始在院子里开辟菜地。三天功夫,原本娇艳的玫瑰花圃变成了一畦畦绿油油的菜地,喷水池里撒满了鱼苗,靠近马路的角落还砌起了一座猪圈。
有人看了直摇头,说这是暴殄天物。许世友却笑得跟个老农民似的:“花只能看看,菜能填肚子,猪还能长膘增重,哪样不比花管用?”
别墅里的装修也被他大刀阔斧地改造了一番。一楼原来的餐厅改成了放农具的杂物间,二楼的客房里塞满了他从广州带来的旧家具:硬邦邦的木板床、掉了漆的旧桌子、破旧的木头椅子。新的军区领导想给他配辆新轿车,他坚决不要,继续开那台已经跑了十几万公里、随时可能趴窝的老吉普车。
每次进城买菜,他都是自己开着这台破车轰隆隆地往菜市场跑,跟小商贩讨价还价,一点将军的架子都没有。警卫员私底下嘀咕“首长真够节俭的”,被他听见了还得挨一顿训:“当兵的人,艰苦朴素是咱们的老传统,不能丢。”
院子里的农活可不少:除草、翻地、修剪枝条、喂猪、捞鱼,一天忙下来手上全是泥巴。1982年大儿子许光来看望他,劝他别干这么多重活,老爷子一拍桌子就不乐意了:“我lei个去,枪林弹雨都没把我撂倒,这点农活算个啥?”
说完摸出口袋里的香烟,递给儿子一根,自己也点上一支,父子俩在烟雾缭绕中聊着家常,那份惬意劲儿是多少年都没体验过的。

有意思的是,由于院子里自产自给,原本的食堂反而成了摆设。早上喝大米粥就两个玉米馍馍,中午晚上基本是两荤两素的搭配——那盘青菜必定是自家菜地里刚拔的,猪圈里出栏的肉不是腌成腊肉就是红烧。
厨师心里直打鼓:这伙食标准对得起副国级干部的身份吗?可许世友摆摆手说:“我现在就是个退休的普通老百姓,别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”
翻开他的作息安排,无非就是干农活、看书、练字这三样事情不断重复。周恩来总理当年送给他的那套《红楼梦》放了二十多年,现在终于有时间一页页仔细品读。他在书页空白处写批注,看到“宝玉葬花”的情节,用钢笔划了一道横线,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:人生变化无常,要珍惜眼前的福气和缘分。
闲暇时抓几张废纸练毛笔字,笔锋刚劲有力,墨香和泥土气息在屋子里交融,分不清这是将军的书房还是农民的小屋。
远在河南新县的老乡们最理解他。“听人说老许住上了大别墅,还在院子里种菜喂猪,这人真有本事!”第二年春天,几个同乡提着腊肉、竹笋坐火车专程赶到南京看他。
许世友一听到熟悉的乡音,眼睛立马就红了,赶紧把礼品往屋里搬:“快进来,先喝碗小米粥暖暖身子。”等老乡们要走的时候,他塞给县里干部一摞棉衣和三千块现金,反复叮嘱:“村里要是有老人家看不起病的,记得给我写信。”

秘书后来算了一笔账,从1981年到1984年这几年里,许世友自掏腰包寄给家乡的各种物资和现金加起来超过了两万块钱。要知道那可是一个离休干部不吃不喝四五年才能攒下的全部工资。
1985年2月,邓小平南下视察工作。火车到了南京站以后,他没有按照安排直接去会场,而是专门绕道来到中山陵8号。门口值班的小战士刚要敬礼,邓小平挥了挥手就径直走进了院子。
两位久经战场考验的老战友围着菜畦慢慢踱步,几句平常的寒暄却格外真诚。“老许,你在这儿过得像神仙一样啊。”“还凑合,就是菜种多了卖不出去,要不要带点回北京尝尝鲜?”一句玩笑话,让秋日午后的笑声格外爽朗。
可惜这份悠闲自在的日子没能持续太久。1985年10月22日凌晨三点,许世友因为肝病恶化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去世,享年八十岁。临终前,他留下了最后的心愿:土葬,要葬在老家鸡公山脚下,还要穿那套补了五次、打满补丁的旧军装下葬。
经过邓小平的特别批准,这位多年来坚持推行火葬政策的中央领导破例为老战友开了绿灯。第二年清明节,新县的山路上挤满了自发前来祭拜的老乡,有人背着一袋土豆,有人提着自家酿的米酒,悄悄放在墓碑前面。他们心里清楚,长眠在黄土下面的,依然是那个喜欢种菜、惦记乡亲们的老许。
经常有人问,许世友晚年的生活到底有多么逍遥自在?答案其实就藏在那片被他从玫瑰花圃改成菜地的土地里,也写在他一张张寄给家乡的汇款单上。脱下了军装的光环,他回到了最朴实的本性,专心跟阳光、泥土、庄稼打交道——日子本来就该这样过,这是他自己说的话。
坦白说,在那个年代,一个副国级干部住着欧式别墅却坚持种菜养猪,这种反差确实让不少人摸不着头脑。可对许世友来说,这恰恰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向往。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,骨子里就流淌着对土地的深深眷恋。

战争年代的硝烟散去,和平时期的荣华富贵对他来说都是过眼云烟,只有那股熟悉的泥土香味才能让他真正安下心来。
丢雷,这就是许世友,一个永远忘不了自己根在哪里的老兵。即使身居高位,即使住进了豪华别墅,他依然选择用最朴素的方式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。种菜、养猪、帮助老乡,这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,却构成了他生命中最珍贵的片段。
现在想想,许世友的选择其实给所有人上了一课:不管爬到多高的位置,不管拥有多少财富和权力,最终能让人感到满足和快乐的,往往还是那些最简单、最纯真的东西。一把泥土,几垄青菜,几声乡音,几个老友——这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东西,却比任何荣华富贵都更能温暖人心。
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许世友宁愿放弃北京的舒适生活,也要在南京的小院子里当一个快乐的“农夫”。因为他明白,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什么,而在于内心的那份宁静和满足。而对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兵来说,还有什么比重新回到土地的怀抱更让人安心的呢?
你觉得许世友这种选择是真的洒脱,还是另有深意?
网上配资开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